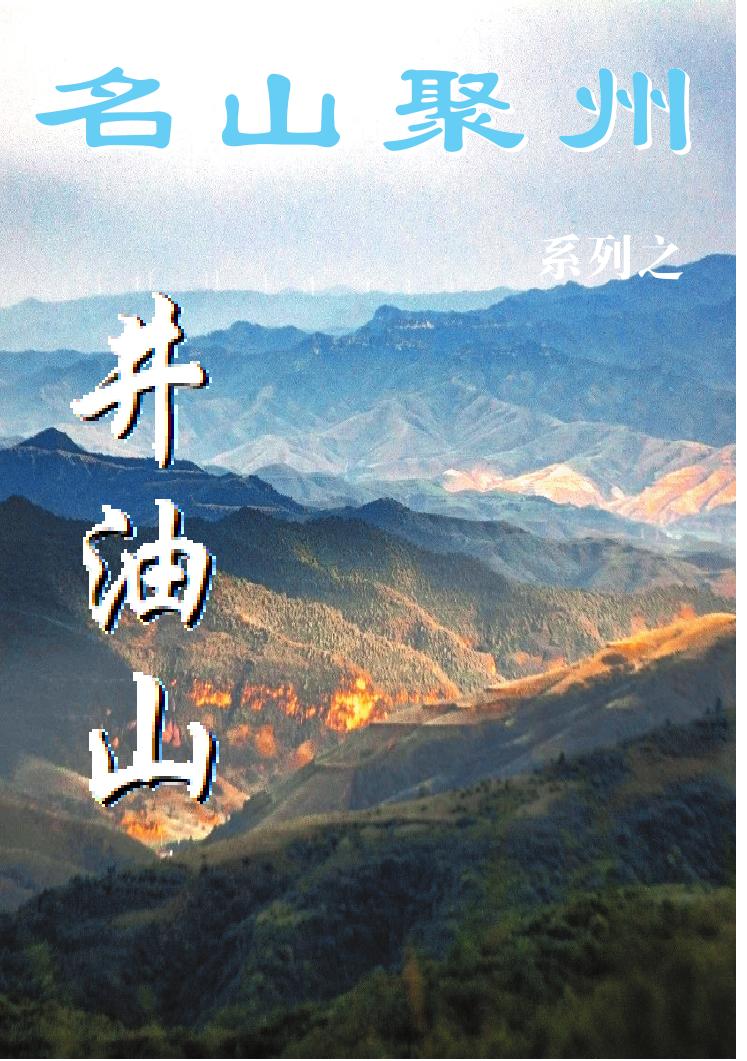
“保德縣是個(gè)好地方��,無(wú)限好風(fēng)光��,井油山上飄彩云,黃河流水萬(wàn)年長(zhǎng)……”一首傳唱四方的保德民歌《保德縣是個(gè)好地方》�����,既勾勒出保德山川的壯美輪廓�,也承載著黃河文化的深厚底蘊(yùn),更讓“井油山”這個(gè)名字��,隨著悠揚(yáng)曲調(diào)走進(jìn)了無(wú)數(shù)人的心里����。
井油山坐落于保德縣東南角,地處保德��、岢嵐、興縣三縣交界地帶�,主峰海拔1548米,為保德境內(nèi)至高點(diǎn)�,山體平均海拔約1506米。這里青山疊翠��、林海浩瀚��,既有保存完好的天然次生林���,也有郁郁蔥蔥的人造林���,堪稱保德最負(fù)盛名的“天然氧吧”——空氣里裹挾著草木的清新,盡是天地饋贈(zèng)的生機(jī)�。
立于井油山巔,風(fēng)光盡收眼底��。遠(yuǎn)山如黛�,似畫師以淡墨隨性揮灑;云霧纏繞�,像仙人隨手拋下的素紗。風(fēng)自山腳徐徐而來(lái)����,攜著青草的鮮嫩與松針的醇厚����,穿入肺腑�。每一次呼吸都如飲甘露,令人心神一振�,旅途的疲憊瞬間消散。八月的山澗�����,細(xì)流潺潺���,其聲悅耳。日光透過(guò)枝葉縫隙����,碎成點(diǎn)點(diǎn)金箔,在山坳間跳躍�,為滿山濃綠注入了靈動(dòng)氣息。密林深處�,時(shí)而傳來(lái)野雞、鷓鴣的清啼��,劃破山間靜謐��;時(shí)而有野兔、松鼠竄動(dòng)的窸窣聲�����,讓整座山都透著勃勃生機(jī)�����。

井油山遠(yuǎn)景�����。王海榮 攝
千年生態(tài)的破局與重生
這滿山盎然綠意的背后�����,藏著一段人與時(shí)光�����、人與自然的漫長(zhǎng)博弈����。
春秋時(shí)期,保德一帶草木繁盛���、森林密布�。《山西資料匯編》記載��,古時(shí)此處曾是林海莽莽的秘境�。《保德土壤》亦提及�����,秦代之前��,這里屬林牧區(qū)��,即便到了宋代���,仍有寬達(dá)25公里的林帶蜿蜒于山間。遺憾的是����,自明代成化年間起,河曲��、保德�����、偏關(guān)一帶成為軍事前線,大規(guī)模修筑長(zhǎng)城�、堡寨,屯田活動(dòng)大面積展開����,對(duì)木材、燃料的需求急劇增加���,大片森林遭到砍伐����。原始森林日漸萎縮��,至清代時(shí)已徹底被毀�,保德境內(nèi)淪為荒山禿嶺,形成常年干旱少雨����,“河曲保德州,十年九不收”的惡劣生態(tài)�。如今境內(nèi)的天然林,多為原始森林被毀后殘留的次生林����,而井油山村南山的天然次生林����,便是其中面積最大的片區(qū)�。
這片次生林的樹種分為喬木與灌木兩類:?jiǎn)棠疽詡?cè)柏、杜松����、檜柏、山楊����、白樺、柞樹����、山桃、山杏為主���;灌木則有沙棘�����、美薔薇��、黃刺玫�����、檸條��、荊條等����。1964年的統(tǒng)計(jì)數(shù)據(jù)顯示�����,其面積僅377.3公頃���,其中側(cè)柏林218.7公頃——稀疏的林木孱弱不堪��,仿佛隨時(shí)會(huì)被風(fēng)雨吞噬���。
為守護(hù)這片僅存的綠意,恢復(fù)植被�、改善生態(tài),1953年,政府派專職干部長(zhǎng)期駐守井油山�����;1955年劃分林區(qū)���、確定林權(quán)�,全面實(shí)施封山育林����;1959年成立井油山國(guó)營(yíng)林場(chǎng),專職負(fù)責(zé)天然林保護(hù)工作����。此后,“三北”防護(hù)林二期工程接續(xù)推進(jìn)�����,一代又一代護(hù)林人在此扎根�,用堅(jiān)守續(xù)寫綠色篇章。他們?cè)跍峡?�、交通要塞設(shè)卡值守�����,靠人工巡護(hù)防范風(fēng)險(xiǎn)��;在牲畜危害嚴(yán)重���,人為活動(dòng)頻繁的區(qū)域����,用鐵絲圍欄����、石料壘墻、開溝挖壕等方式筑牢防護(hù)網(wǎng)����;在自然繁育能力不足、幼樹分布不均的地塊�,通過(guò)補(bǔ)植補(bǔ)種、平茬復(fù)壯����、抗旱保苗等措施,助力森林恢復(fù)更新���。
多年耕耘終有回報(bào)�����。如今的井油山�����,森林連片延展���,實(shí)現(xiàn)了四季常青����。據(jù)統(tǒng)計(jì)�����,其有林地面積達(dá)7713公頃��,其中側(cè)柏林480公頃���、灌木林3253公頃��,森林覆蓋率高達(dá)63%���。經(jīng)林業(yè)部門測(cè)算�����,這片森林每年可涵養(yǎng)水源203.6萬(wàn)噸,減少流入黃河的泥沙677.5萬(wàn)噸��。昔日荒蕪的“禿嶺”����,終于變回了四季常綠的“綠毯”——這是人力與天工攜手,在時(shí)光里織就的生態(tài)奇跡�����。

井油山林區(qū)���。王海榮 攝
藏在歲月里的故事與風(fēng)骨
民國(guó)《保德地理志》記載:井油山�����,系岢嵐山支脈��,道路崎嶇����,地勢(shì)遼闊?!俺俏髂厦妫貏?shì)僻靜����,居民寥落?���!绷攘葦?shù)語(yǔ),勾勒出這座山的地理特質(zhì)與過(guò)往印記�����。
山林深處�����,藏著一個(gè)與山同名的村落——井油山村����。村民以農(nóng)耕、畜牧為生�,性子如山間清泉般淳樸����。村口觀音廟旁�����,有一棵老柳樹��,樹干粗壯需兩人合抱����,樹上懸掛著一口蔡氏大鐵鐘���。鐵鐘上書寫的字跡雖已斑駁��,卻清晰道出了山名的由來(lái):古時(shí)村民聚居于此�,飲用水源卻遠(yuǎn)在深溝之中�����,水貴如油���,故得名“集油山”�,年深日久,逐漸演變?yōu)椤熬蜕健?�。廟旁曾有一棵同樣粗壯的老榆樹�,枝葉繁茂能遮蔽烈日,可惜在1973年被砍伐��,只留給后人一段悵然的回憶�����。
村里的老人總愛講起井油山的舊事�����。他們說(shuō)��,這里曾是周邊賀家山����、青菅圪垯、木瓜棱���、紅林溝���、馬泉峁��、圍梁���、安子峁、樺嶺塔���、張家墕等10多個(gè)小村的集散地�。過(guò)去每月逢初五�����,村民們都會(huì)帶著自家物產(chǎn)來(lái)此趕集�����,如今殘留的爐灰����、炕板石遺跡���,仍能讓人想見當(dāng)年的熱鬧景象�。1954年����,當(dāng)?shù)卦O(shè)立井油山鄉(xiāng)����,但因地處偏遠(yuǎn)�、地廣人稀,10多個(gè)小村的總戶數(shù)加起來(lái)不過(guò)百戶�����,1956年便并入了東莊墕鄉(xiāng)��。更古老的傳說(shuō)里�����,井油山村南面的楊家山墕�����,曾是北宋楊家將楊六郎的馬場(chǎng)�。這片區(qū)域東至岢嵐八龍廟,南至興縣青草溝村��,西至興縣西坡村,北至井油山村�����,東西綿延30華里����,南北縱橫約3華里。此處坡地廣闊���、林木茂密���,如今仍是周邊村民放羊的好地方。據(jù)說(shuō)�����,每逢天陰下雨����,山林間仿佛還能聽到戰(zhàn)馬的嘶鳴��,讓人遙想當(dāng)年楊家將的鐵血風(fēng)采�。而村東的刺沖圪垯,曾有猛虎出沒(méi),騷擾耕牛�����、傷害農(nóng)人����,為這片山野添了幾分蒼涼與神秘。
這片土地不僅有故事�,更有熱血風(fēng)骨。20世紀(jì)30年代�,黨的地下組織便在此成立。到40年代全縣解放時(shí)���,井油山一帶已有5名老黨員�����。烈士郭八圪爪��,1902年生��,1938年9月加入決死隊(duì)�����,同年12月在保德戰(zhàn)斗中壯烈犧牲����。他的名字與事跡,早已融入井油山的精神血脈��,成為永不磨滅的印記����。

井油山村一景。吳 宇 攝
從“養(yǎng)窮人”到“藜麥之鄉(xiāng)”的蛻變
井油山地處三縣交界�,山高林密、人少地多����,兼具農(nóng)耕與畜牧的天然條件。在過(guò)去的災(zāi)荒年�,保德、興縣的窮苦人為謀生計(jì)����,要么“走西口”去內(nèi)蒙掏甘草,要么就翻山越嶺來(lái)這里墾荒——因井油山與岢嵐接壤���,當(dāng)?shù)厝怂追Q這種行為為“爬岢嵐”。井油山也成了遠(yuǎn)近聞名的“養(yǎng)窮人的地方”。
那時(shí)��,這里種植的作物除了山藥��、糜子����、谷子、玉米等大宗農(nóng)作物����,還盛產(chǎn)莜麥、胡麻����、黃芥等特色作物。每到秋收時(shí)節(jié)����,山下的腳商便會(huì)趕來(lái),用紅棗�、醬醋或鍬镢犁耙等物資,換取村民手中的莜面��、黃油�、羊皮�����,以物換物的交易聲���,曾是山間最鮮活的煙火氣。
時(shí)代的車輪滾滾向前�����,井油山的產(chǎn)業(yè)也迎來(lái)了新的發(fā)展��。2013年�,井油山村引進(jìn)藜麥種植,經(jīng)試種發(fā)現(xiàn)畝產(chǎn)可達(dá)400斤���,且市場(chǎng)前景廣闊���。2015年,村民郭保國(guó)種植20畝藜麥����,當(dāng)年便收入4.8萬(wàn)元。在他的帶動(dòng)下�,村民們紛紛加入種植隊(duì)伍�����,藜麥種植面積很快達(dá)到500畝,村民收入顯著增加��。井油山也成了全縣知名的“藜麥之鄉(xiāng)”�。
立于山頂,看林海翻涌���,聞藜麥飄香�,方能真正懂得:井油山的美����,不僅在于自然的靈秀、歷史的厚重��,更在于那生生不息的人間希望�����。
山還是那座山�,卻因一代代人的執(zhí)著堅(jiān)守與自然的慷慨饋贈(zèng),完成了從荒蕪到豐茂�����、從寂寥到喧騰的蛻變。這跨越時(shí)光的轉(zhuǎn)變����,便是井油山最動(dòng)人的敘事。(馮云)
(責(zé)任編輯:盧相?����。?/span>